
10月18日下午,“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坛”第六讲在37000Cm威尼斯天挺阁举办,特邀嘉宾是著名医学史专家,德国利奥波第那国家科学院院士、杜塞尔多夫大学原校长阿方斯·腊碧士(Alfons Labisch)教授。讲座由37000Cm威尼斯院长余新忠教授主持。讲座开始前,余新忠院长对阿方斯·腊碧士教授做了简要介绍,并致送“南开史学百年大讲坛”主讲人聘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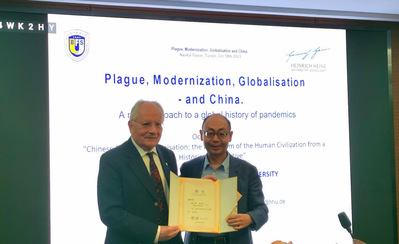
腊碧士教授首先以一些宏大问题开启讲座,例如疾病与全球化、现代化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21世纪的第一场疫病SARS如何影响世界。讲座共分八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人类、自然与文化之间的关系。腊碧士教授认为,人类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在人体内及周围生活着大量的病菌和微生物。同时人类在与自然的互动中形成文化,并用这种文化来解释、命名和认知疾病。因而人类的疾病不仅具有自然属性,同时也是社会活动及文化环境塑造下的产物。
讲座的第二部分腊碧士教授介绍了有关疾病和瘟疫的人类学及历史学研究,主要论及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和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戴蒙德认为人类的疾病和健康状况主要由他们就近的生活环境决定,麦克尼尔则将视角放宽至全球,认为瘟疫和流行病将世界的历史紧密联系在一起。
讲座的第三部分有关早期流行病的历史记载。腊碧士教授指出,新石器时期农业发展,人口增长,人与动物共居的生活方式出现,使得地方性的传染病有可能扩散为更大范围的流行病。考古和分子生物学的研究表明,最早的流行病发生在距今约6500年前,有关流行病的记录首次出现于公元前2000年。在中国,自公元前770年起已经有关于周期性疫病的记载。在两千多年的帝制历史进程中,流行病影响了中国的人口结构。中国很早就有个人防疫行为及防疫药物的相关知识,然而系统的防疫机制则要等到清朝晚期才发展出来。总体而言,人类文明早期首次出现了有关世界性流行病的记载,但尚未形成持续性的公共防疫措施。到了中世纪,出现了反复爆发的流行病的记录和最早的公共防疫举措,例如隔离,控制商品流通,卫生监察,雇用城镇医生等。
讲座的第四部分有关流行病的历史解释模式,腊碧士教授介绍了三位主要学者,分别是克罗斯比、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以及米科尔·格梅克。克罗斯比提出了著名的“哥伦布大交换”概念,处在这种交换当中的不仅有动物、植物、贵金属、商品,还有病原体和流行病。埃马纽埃尔·勒华拉杜里认为世界被不断扩张的交通网络连接在一起,病原体以及它们的天然宿主也经由这张网络传布到世界各地,由此导致“世界微生物的一体化”。米科尔·格梅克认为流行病与人类社群自身的特征、病原体、自然环境、社会文化环境等各种因素相关,应采取动态且全局的视角综合考虑各种因素之间的互动关系。

讲座的第五和第六部分有关19-21世纪全球化、现代化与流行病的关系。工业革命以及机械化生产推动了全球大宗贸易的发展,物质、商品、服务、人口的流动将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霍乱是当时主要的传染病。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对抗传染病的过程中,昂贵的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在城市中建立起来,个人和群体也被要求采取符合卫生要求的行为。此外,为了防止疫病通过全球贸易传播,各国签署了第一份国际卫生公约。这些西方的公共卫生理念经由日本传入中国。1918年爆发了西班牙大流感,这场疫病说明在真菌、细菌等传统的传染媒介之外,还出现了新的致病因素,即能够持续变异的病毒和病原体,世界由此进入了“新兴疾病”的时代(the age of new emerging diseases)。腊碧士教授认为我们必须清晰地意识到未来还会爆发疫病,防疫需要全球性的监测和防护体系。

讲座的第七部分腊碧士教授探讨了21世纪初的SARS疫情以及中国的应对,认为中国积极地从SARS疫情中吸取经验教训,发展出一系列防疫措施,例如限制野生动物市场,建立快捷的传染病信息系统,加强健康卫生教育,对人传人病例进行特殊护理,开发疫苗等。这些举措在抗击H1N1流感以及新冠肺炎中都发挥了积极作用。
讲座的结语部分,腊碧士教授提出了两个仍待思考的问题:其一,地区、国家和全世界应该采取哪些措施来确保新出现的病原体不向外扩散?其二,如何用历史的分析来理解和认识这些新的病原体?腊碧士教授认为,人类、动物、自然、疾病之间存在紧密且多元的联络与互动,建设全方位的卫生基础设施对于全世界而言十分必要。

问答环节,来自医学院的刘赵昆老师、37000Cm威尼斯袁玮蔓副教授,以及余新忠院长就各自的疑问与腊碧士教授进行了积极讨论。最后,余新忠院长表达了对腊碧士教授的感谢,并期待未来能与腊碧士教授及德国青年学者进行更多学术交流。腊碧士教授也表达了邀请中国学者赴德访学的诚挚心愿。讲座在热烈的掌声中结束。